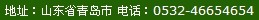|
作者=维舟 来源=年6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变革多在朝代鼎革之际,如殷周、秦汉、隋唐、元明之交均是;但唯有中晚唐和晚清是显著的例外,这种新的变革是在中央的旧外壳依旧保留的情况下缓慢过渡到新的体制。何以这两个王朝能展现出惊人的顽强和韧性,竟能挺过一次次严重政治危机的打击,“本该“结束的王朝又延续了数十乃至百余年,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课题。 从历史上看,一个中国王朝在经历一次动摇根本的危机之后,通常中央权力就难以复振,政治活力往往就此落到地方(如东周、东汉末、北魏晚期、晚清等都是),换言之,像五代十国这样的割据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早该”出现了,然而中晚唐时期的朝廷力量仍活跃在舞台上,只是在遭遇到更严重的挑战之后才逐渐衰微下去,这种强韧的生命力和自我调适能力究竟从何而来? 对此,一个方便的解释或许是:“安史之乱”爆发之际的唐朝本来就并非已衰落到不堪一击,其本身就还相当强盛,因而朝廷虽然屡屡失误,但仍能调动力量、运用策略,将藩镇割据限制在一个局部地域范围之内。在这种应对全面危机的过程中,朝廷可选的策略是一贯的:充分利用皇帝权威和大唐的合法性资源;稳固尚在掌控之中的地域;强化既有资源的汲取,并建立直属中央的军事力量(禁军);运用纵横术的谋略来分化和打击个别不服从的藩镇;在贵族和节度使这样更具自身独立性的中层力量之外,从出身更卑微的阶层(不论是宦官还是底层文士)中寻求更依赖于皇权的同盟者。实际上,除了皇帝权威及其合法性资源之外,朝廷的做法与那些与它竞争的藩镇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陆扬 可以说,在中晚唐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政治现象:一方面是中央和强藩为重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参与及政治权力的向下渗透。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不无相似之处,即皇帝不得不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并为了在斗争中获胜而向下寻求支持。 在此情形下,所谓“清流文化”成为一种新型政治精英的评判标准,与之前那种以郡望、世家或官品的身份不同,清流文化强调的是“文”的素质与特定资历的结合,换言之,它更基于个人才能而非血统等“给定的”因素。按照陆扬的论述,唐代是“文”作为精英最高价值取向的关键性转折时代,这种“文”与皇帝权威的核心的政治形态高度结合,明确“‘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其实质是要凸显皇帝的权威和个人魅力”。然而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皇权的加强,在当时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恐怕是为了应对危机和重新整合帝国的手段。 陆扬虽然自问“为何到了唐代,‘文’才真正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衡量标准呢,这种‘文’的具体内涵外延又如何把握?”但自问之后并未自答。在我看来,这同样是对安史之乱这一危机的应对。很奇怪,陆扬未曾提及韩愈这一重振儒家的关键人物,他振衰起弊,正是为了重树儒家的文教理想。此外,清流文化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为中晚唐文学普及、渗透到更低阶层的结果。固然,从科举制中寻求出身社会下层精英、更多依赖皇权而较少具备独立性,然而书中也举出张九龄和裴枢等的例子,表明这种清流文化实际上与最高统治者取向颇有不同:皇帝看重的往往只是“吏能”,然而清流精英却敢于顶撞帝王,坚持自己的评判标准。 莫高窟中反映晚唐日常生活的壁画 这涉及到这一新的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是否能保证其独立性。而从结果来看,在握有实权的人物面前,这种独立性难有保障可言。按陆扬的论述,藩镇诸侯竭力延揽文士,是因受到唐廷倡导的以“文”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渗入,但很显然,从朱温、赵匡胤等人的言论来看,藩镇诸侯对文士所推崇的最高价值并不认同,他们倒不如说看重的只是他们的“功能”。也就是说,政治家(尤其乱世政治家)看重的是能力,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执行权来进行统治,但这会被中国传统儒家政治视为霸道,而文教则认为政治事务的最高使命在于“人文化成”。此类观念的冲突即便到晚清仍是。 书中另一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提到唐代政治理念和运作中“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固然是得自西方著作中“国王的双重身体”,但在此的确可以解释一系列现象,他进而主张“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不仅如此,他认为“从德宗以来,皇帝在唐代政治格局中所能发挥的权威越来越基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皇权。作为个人的皇帝要能真正发挥稳定政局的作用,就必须依照此种新政治格局的要求来行事,否则即便有求治之心,也难以达成目的”。但中晚唐的皇帝之所以起用宦官来掌权,架空外朝,是因为中央官僚系统与“地方藩镇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吗?恐怕不是。实际上倒不如说,皇帝的行事在诸多方面越来越像藩镇诸侯:同样依赖私人军队,同样任用更具人身依附性质的亲信——在他们眼里,宦官原只是“家奴”。 唐德宗李适 制度化皇帝权威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他强调,“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终要靠皇帝来维系”,“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代表的主要是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话虽如此,但新体制的建立本身,其实就与唐宪宗顽强的私人意志有关,只有这样强势的皇帝才谋求绝对控制权,既然他在当政后就迅速改变游戏规则,也可见原有的制度并未能对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形成有效约束。这一点在中国史上屡屡如此,即便到了文革时代仍是如此。 按陆扬的理解,中唐元和时期中枢政体的运作,“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政治和行政的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否认宦官力量恶性膨胀以侵蚀或支配外廷官僚。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很奇怪的,他未提及一点,即外廷官僚当时并不掌握关键的禁军军权。在中国史上屡屡有这样的现象:新的军事力量一旦涌现,即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说白了,宦官力量的支撑不在于皇权的赋予,而在于军权。一旦军权旁落,朝廷战败,“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邠岐,南衙北司(分指文官与宦官)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在这样一个实力至上的时代,最后都是暴力的掌控者说了算。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陆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3月 从某种程度上说,皇权的双重性可以这样解释:帝王的私人意志放大到极端,即是专制;而机关化到极端,则是立宪君主。在前一种情况下,君主权力是任意的、无限的,而后一种情况下则是有限的、非个人化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前夕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天皇机关说”,认为天皇的权力不是其个人的,而是国家行为,天皇只能按宪法规定的来行事。陆扬在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拈出皇权的双重性作为分析重点,不无卓见,但他说的皇帝权威的“体制化”,显然并不是一套具有约束性的、明文规定的政治共识。不妨这么说:唐代中国会选择立宪君主吗?显然,即便是晚唐诸帝,也不甘于成为无实权的“立宪君主”,而他手下这些人也并非独立行事的贵族。事实证明,晚唐五代政治的发展,是集权而非分权,中国的统一,常常都是沿着权力再度一元化的路径。虽然他强调晚唐皇帝的权威,但从唐衰到宋兴,靠的也不是旧有中央权力模式的重振,新的权力中心其实起自藩镇,或者说,中央也藩镇化了,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即要求绝对效忠于一元的权力中心。 “长乐老“冯道 从这一点来看,全书所真正论述的应是中晚唐某种政治统治模式的确立,而非仅是“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因为作者似乎暗示,中晚唐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这个看似纷繁混乱的时期孕育了新的体制和新的可能。不过奇怪的是,在一个权力政治的时代,他往往略过那些真正影响政治体制兴衰的因素(尤其是军权),而更注重“势”和无形力量对政治趋势转移的影响,这种敏感除了学术训练和新的学术热点因素之外,或许也是“循性为学”?因为在行文叙述中可以发现,他偏好复杂多变的事实、多样化的细致解读、绵密的论证,不时强调“历史想象力”和“分寸感”,从他对陈寅恪和内藤湖南观点的异议来看,他对粗线条概括的分析模式“尤其不赞同”,偏好错综微妙之处。他看来讨厌社会学式的模型归纳,在他看来每件事都是不一样的,因而每每沉浸到历史细节中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而这也容易导致一种史学家尤其易犯的错误:迷失在细节中(lost in detail),从而会绕进一些琐碎的历史事实来否定整体性的理论概括,这也会导致过分纠缠于一些具体事件。如果说他对前辈学者的不满是觉得“见林不见树”,那或许他本人正有某种程度上“见树不见林”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书评 eeobook 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合作及投稿邮箱:eeobooksina.白癫风是什么初期白癜风能治愈吗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qingliuzx.com/qlxhj/1170.html |
当前位置: 清流县 >晚唐帝国的落日余晖清流文化的终结
时间:2018-1-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文化清流柳传志遇见失败,是每个人都必经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