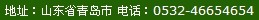|
(四)阿鼠 年冬天,当河子夜晚陶醉在女人的芬芳时,阿鼠依然穿着我母亲送给他的、我哥穿过的旧警察制服,整日在街上捡烟屁股抽。每次他路过王佳的修表店时,王佳总是欢快地叫声“阿鼠”,然后迅速从旁边男人手里抢过烟,扔到阿鼠手里。 这时的阿鼠,兴奋得两眼放光、鼻涕横流。他抚摩着那根珍贵的烟,朝王佳竖起拇指:“佳……好人!”王佳一听这话,高兴地咯咯直乐。旁边烟被抢的男人也陪着傻笑。这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幕:两个身体都不健全的人,读懂了彼此的善意。 曾经有一次,一个男人妒忌王佳对阿鼠的好,等阿鼠把烟夹在耳朵上,抬头看河边树上的鸟窝时,他从后面窜出,故意把阿鼠撞进小河里。那是冬天,河上的薄冰哗啦啦碎了一个窟窿,阿鼠在刺骨的水里扑腾了几下,就沉到了水底。男人慌了,从墙角抓起一根竹竿伸到冰窟窿里。一会儿,阿鼠湿漉漉的手从水里伸出抓住竹竿,接着他的头浮出,他抓着竹竿一点点漂移到了岸边。 上了岸,他嘴唇发紫,全身瑟瑟发抖。但奇怪的是,那根烟始终夹在他的耳后,因为浸泡了水,显得有点垂头丧气。捉弄他的男人无比沮丧,扔下竹竿无趣地走了。 清流镇在闽东山区,如果你到这里,一定会颠覆之前福建气候温暖的印象。一到冬天,清流镇就天寒地冻,稻田里的水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里面凝结着绿色的鸭屎。但我们并不在意,在稻田的水还缓缓流动时,我们就早有预谋地从家里偷出几根粗粗的绳子,一头用石头压在田埂上,一头垂到水里。次日上学时跑到田边,发现水已结冰,只需轻轻一拽,就轻易拉起一块冰。我们快活地吃着冰往学校走,然后在老师严厉的目光中把冰扔在教室门口,碎了一地晶莹。 之所以对童年场景作以上大段的回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那段乡村时光的留恋,更重要的是,我想说明,在清流镇滴水成冰的冬天,阿鼠掉进河里还能活着爬上岸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阿鼠被撞进河里的消息很快传到王佳耳朵里,她把那个恶作剧的男人臭骂了一顿,并让他滚出店去。别的男人为讨好王佳,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奚落他。这宣告着那个男人快乐生涯的结束。他从此象幽灵一样在王佳的修表店外游荡,有时他无聊地坐在街对面,看着别的男人自由进出王佳的店,眼里满了忧伤。 我不知道王佳除了漂亮,还有什么别的魅力让所有的男人都忽略了她萎缩的双腿,而对她众星捧月?也许,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女人脸蛋漂亮就足够了,至于脑容量多少,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因为男人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脑容量来考虑这些问题的。 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清流镇估计除了阿鼠,别的男人都把王佳当成梦中情人,甚至包括我的父亲,李家兴镇长。某天,母亲下乡抓计划生育工作,他以修钟为名,堂而皇之走进了王佳的表店。 其实这只钟只是没有电池了。我在头天晚上看见父亲鬼鬼祟祟地从墙上拿下钟,取出电池,换上了一节已经废弃的电池。父亲走在路上时神情有点慌张,他故作镇静地向每个人打招呼,未等别人询问他去哪里,他就故意扬一扬手里的钟,说:钟不走了,看来要去王佳那里修一下了。 父亲的到来让王佳很吃惊。她客气地让父亲坐下,然后把钟拆开,最后发现是电池没电了,就帮父亲换了一个,整个过程花了不到十分钟。父亲接过钟后懊悔不已:早知道这么快就换完,应该把钟泡在水里。但我知道父亲是舍不得的,那个钟是父亲去上海开会时买的,几乎花了父亲半个月的工资。 当然,可怜的阿鼠是不在这些男人之列的。他甚至分不清男女,又如何能向往男女之事呢? 有一次,镇上来了一个贩卖地瓜苗的外乡女人。她身材丰满,两只硕大无比的乳房似乎要从薄薄的衬衣里喷薄欲出。每当她俯身整理瓜苗时,露出的半边乳房宛如一堆甜腻的糖浆,上面粘满了男人苍蝇似的目光。 只有阿鼠例外,他对这一切毫无知觉,似乎对树上鸟窝的兴趣更甚于女人。不过在别的男人的撺掇下,他还是涎着脸向女人索要一毛钱。女人很痛快地给了他,这让阿鼠高兴地无以复加,他一整天都在女人的拖拉机上活跃地跳上跳下,帮她卖地瓜苗。 街边店里坐着的一堆男人指着女人高声问:“阿鼠,你知道她是男人还是女人吗?” “不知道!”阿鼠头也不抬。 “快说,我给你一毛钱!”一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用手拨拉一下,钱响得很欢。 也许是一毛钱的诱惑太大了,阿鼠看了女人一眼,转过头说:“男人!” 人群爆发出一阵笑声。又有人大声问:“那你敢摸她吗?再给你一毛钱!”这个刺激的建议让很多男人的心跳加快。“摸一摸,摸一摸。”很多人附和。 阿鼠可能受到群情激昂的影响,就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在女人肥硕的屁股上摸了一把。毫无防备的女人愣了一下,等她回过神来,就把手里的地瓜苗往阿鼠脸上一扔,然后把阿鼠踢倒在地上,抓起身旁的地瓜苗,塞到阿鼠嘴里,把阿鼠憋得满脸通红。“姑奶奶叫你摸,叫你摸!”她左右开弓,把阿鼠打得鼻青脸肿,在地上趴了半天才起来。 男人们看着,妒忌得眼珠发绿,恨不得压在女人身下的是自己,而不是阿鼠这个傻瓜。于是他们愤怒地把阿鼠从地上拉起来,尽早结束他的艳福。 但河子并不这么想,只要有热闹看,他就觉得很开心,全然忘了自己女人和别的男人私奔的伤痛。他看到阿鼠从地上爬起来,就走过去发出善意的邀请:“阿鼠,我们去打桌球吧。” 阿鼠扯掉嘴里的地瓜苗,激动地问:“真的?”镇上的人都知道,阿鼠最喜欢和河子打桌球了,他们有事没事就到王春平的店里打桌球。每次他们一出现,好心的王春平一边忙着擀面,一边挥着沾满面粉的手,说:随便打,随便打。 阿鼠和河子是镇上唯一一对被允许免费打桌球的搭档,每次他们拿起球杆准备开战,王春平的小店就人满为患。大家都伸长脖子看他们表演。我曾经因为好奇,也观战过一次。只见阿鼠把球杆往旁边一放,然后往掌心吐口痰,捋起袖子就开球。他见球没有进洞,趁河子不注意时偷偷捡起一个球扔到洞里。岂料河子也不傻,他一眼就瞥见了,冲过去把球拿出来,让阿鼠接着打。阿鼠一杆过去,球飞到地上,镇上的孩子就把球放进洞里,然后大叫:阿鼠赢了,阿鼠赢了!阿鼠乐得直拍巴掌,河子气得扔下球杆。当然也有孩子帮助河子把球扔进球洞的时候,阿鼠也一样抗议。有时他甚至和河子打起来,旁边的围观群众乐呵呵地看着,他们一边大声叫好,一边腾出更大空间让他们发挥,如同观看困兽斗。 直到王春平敲着擀面杖大声说,你们下次再打架就要收钱了,两人这才住了手。 我一直感到很奇怪,阿鼠连男女都分不清楚,如何对打球的输赢如此明了?从这点上看,他的智商一点都不低。 阿鼠和河子,就这样消磨着清流镇悠长沉闷的岁月,也被人们消磨着。 ————End———— 作者林世钰,前媒体人,传记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和《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籍。后者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一苇杭之渡彼岸
|
时间:2020/8/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订天芳悦潭年夜饭,极品氡泉免费泡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